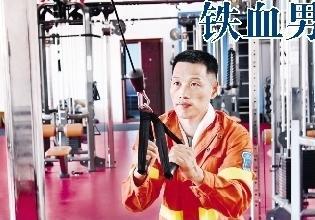
本报记者 赵宇飞/文 孙国祥/摄
当井下警报撕裂黑暗,总有一群人身披橙色战甲逆流而上。今年46岁的赵守峰在矿山救护战线鏖战二十七载,用一次次赴汤蹈火的无畏和执着丈量责任、镌刻忠诚,从青涩学徒到铁血教官,从生死战场到育人讲台,始终以矿工之子的赤诚在千尺井巷奏响一曲曲“向死而生”的英雄赞歌。
铁骨熔炉锻真金
赵守峰的父亲曾是桃山矿的老矿工,小时候他总蹲在原七台河矿务局职工家属院的柳树下听父亲讲井下挖煤的故事——黑暗里的矿灯、岩层里的汗珠、矿工间的扶持,还有那句“井下人命关天”的叮嘱。
跟随赵守峰思绪,走近他的故事会感受到青涩与倔强。
1998年,赵守峰带着一腔热血走进了公司救护大队。可现实远比想象残酷,一米八的大高个儿,体重却不过百斤,训练时扛着近50斤的呼吸器和灭火器,走两步就踉跄。
“当时觉得这铁疙瘩比我还沉。”他笑着回忆。
改变发生在一次常规训练。那天,赵守峰扛着设备跑了半公里,累得实在撑不住了,“咚”地把呼吸器甩在地上。“这设备的确沉重,但比它更沉重的是承载的生命重量,你知不知道设备摔落也会爆炸的,立刻给我捡起来。”时任公司救护大队桃山中队队长吕志波的吼声里带着怒气。
赵守峰红着眼捡起设备,一步一步往回挪。几公里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心上。(下转四版)(上接一版)回到宿舍,他对着床板猛捶自己的腿:“我算什么男人?连这点苦都吃不了!”那晚,赵守峰翻来覆去睡不着,父亲的话突然清晰起来:“守峰,咱们矿工的命是拿汗水换的。救护队员的命是拿命换的。”从那天起,训练场多了个“不要命”的身影。别人跑5公里,赵守峰跑10公里;别人练呼吸器操作1小时,赵守峰练3小时。赵守峰手掌磨出的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最终变成厚厚的茧子。吕志波拍着他的肩说:“这才像个救护兵。”
出征战场,与生命的“第一次对话”让赵守峰记忆犹新。
那是赵守峰参加工作一年后的正月十六,地方煤矿发生爆炸事故,这是赵守峰第一次实战,任务是转运遇险者。
井下灾区,瓦斯味混着粉尘刺得人睁不开眼。当找到第一位遇险者时,赵守峰的呼吸几乎停滞了,他说:“那名遇险矿工,像是临死前还在挣扎着要冲出去。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在无声地说你们能救我吗?”多年后,赵守峰说起这一幕仍声音发颤。
第一次冲进灾区开展救援,说不胆怯是假的。“练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峰你能完成任务吗?”赵守峰咬着牙应下队长的询问,壮着胆大声地说:“我能!”
遇险者也是有尊严的。转移途中,四号遇险者与另一位遇险者的胳膊挽在一起,呈现出营救的姿态。那一刻,赵守峰突然明白,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你安心,我带你们回家。”随即,赵守峰弯下腰,艰难地把两个人分开,顺利完成了遇险者转运任务。“我们这份工作会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分量,哪怕生命已经消逝,也要让他们体面地离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救活人,也要护好逝者的尊严。”这句话,成了赵守峰此后救援生涯不变的工作信条。
铁血烈焰砺锋刃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一身正气甚至有些倔强的赵守峰在一次救援时红了眼眶。
2011年8月23日,七台河勃利县恒太煤矿四井发生透水事故。接到救援任务准备深入井下灾区救援的赵守峰看到泪眼婆娑的家属心里一揪,虽然没有言语交流,但对视的那一瞬间让他顿感使命重大,一定要完成任务给家属一个交代。
“我当时负责测量水位,探查灾区灾情。”赵守峰说,巷道里的水已经满溢,矿灯照出去一片混沌的白,我站在顶板上面测量水位,探查灾情。在井下,根本分不清昼夜,时间在哗哗的水声里成了模糊的概念,赵守峰每半小时必须向指挥部汇报一次水位,每一次报数都像在给黑暗里的希望划刻度。
当水位慢慢降到胸口位置时,赵守峰摸到岩壁上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眼儿。他艰难地爬了进去,水顺着安全帽檐灌进衣领,后背的呼吸器压得肩胛骨生疼。根据经验,赵守峰初步判断被困矿工就在这附近区域。
“多往前一米,就多一分希望。得赶快往里进。”赵守峰心里直犯急。
水位慢慢下降,赵守峰作为突击队员第一个跳进巷道,蹚着漫过胸口的积水,摸索着往前挪。往前挪了10米左右后,赵守峰发现水面突然泛起光影。“光。”赵守峰猛地抬头,心跳声盖过了水声。“有光源就有人活着。”赵守峰用颤抖的声音高喊,随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救援指挥部。
探杆往光的方向探去,赵守峰发现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带着哭腔说:“里面还有十几个人。”赵守峰带领队员毫不犹豫地冲向前,把被困矿工转移到安全地带。
当最后一名矿工被托出水面时,晨光正漫进井口。“都好好的,放心吧!”赵守峰与被困矿工升井后,再次看到家属们喜极而泣的神情,他的鼻子突然一酸,泪水混着巷道的积水和汗水糊了满脸。这不是软弱,是压在赵守峰心里的使命感,终于在此刻有了回应。
后来有人问赵守峰:“当时怕不怕?”他摇头说:“怕什么?井下的人在等,家属的眼泪在等,咱救护兵的命就是用来给这些人托底的。”
那一束光,赵守峰记了一辈子;那天的泪,赵守峰也记了一辈子。不是因为苦,是因为赵守峰明白,救护队员流的每滴汗、受的每处伤都是给家属的“定心丸”。
事故发生时,别人都是想着往外跑,救护队员却是逆行者。2012年,双鸭山一地方煤矿井下突发火灾,公司救护大队集结赵守峰等救援骨干前去支援。抵达矿区时,当地队伍已连续工作12小时却未能探明核心灾情。
救援刻不容缓。救援经验丰富的赵守峰换上防火服,背着氧气瓶和检测仪,在巷道中艰难推进。巷道顶部不断有高温水滴坠落,赵守峰的防火服很快被烫出细密气泡,呼吸面罩的雾气模糊了视线,赵守峰不顾个人安危最终挺进灾区核心区域,每20分钟向指挥部传回气体含量、空气温度、水位温度、二氧化碳浓度等信息,为指挥部提供翔实的第一手灾区资料。
行至井下二水平时,赵守峰发现三节失控的矿用探车如钢铁屏障横亘通道。“必须把探车移开,打通救援通道。”赵守峰迅速观察巷道结构,发现探车后方有半米宽的三角空隙。赵守峰立即与其他人员分工:两人用防火毯裹住手掌卡住探车边缘,另一人用撬棍顶住巷道壁作为支点。赵守峰率先趴在地上,用肩膀抵住撬棍末端,嘶吼着:“一、二!”探车在众人推动下摇晃着移动半寸。“换人。”赵守峰抹了把脸上的汗水,队员轮番顶住撬棍,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探车终于移开了,救援通道也随即畅通了。支援救援任务结束后,指挥部领导拉住赵守峰磨出血泡的手掌说:“辛苦了!感谢你们!”
作为公司救护大队的骨干,赵守峰累计参与处置重大矿山灾害事故20余起,在生死攸关的救援现场,他总是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凭借精湛的技术和无畏的勇气,从灾害现场救出60余名矿工,成为矿工心中的“安全卫士”。
铁汉匠心育新竹
2024年末,公司救护大队新入职18名救护队员,其中有9名大专以上学历的队员被编入加强小队,由经验丰富的赵守峰担任小队长。
带队伍难,带年轻队伍更难。
半年时间,加强小队的队员实现了从“家中娇子”到救援先锋的蜕变,蜕变的根源来自赵守峰那句“要求队员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的朴素承诺。
“现在的年轻人跟我当年不一样,吃不了苦挨不了累。”谈及带队伍的初衷,赵守峰坦言,思想破冰是第一步。组建队伍的第一天,赵守峰没有急于训练,而是向队员讲述老队员在矿难现场连续奋战的往事,还有自己的救援经历,让新队员放下优越感,认清职业分量。
真正的蜕变始于训练场。作为曾多次在省、市技术比武中摘金夺银的“老把式”,赵守峰始终践行要求队员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的原则:打密闭时他第一个趴在狭窄空间里一锹一锹砌砖,手掌磨出血泡也不肯歇;在心肺复苏训练中,他跪在模拟垫上反复按压,膝盖青了一片仍在纠正队员手法;接风机、爬高梯这些“体力活”,他总冲在最前面,用行动代替说教。
“我做不到的,绝不会让你们做;我能做到的,你们必须做到。”从冬雪到夏雨,赵守峰带领队员一同训练,最初2000米跑需要12分钟的队员们半年后全员突破10分钟,最快的7分半就能冲过终点;曾经连单杠都挂不住的新兵,现在最少能做15个引体向上;爬升训练平均高度从3米跃升至4.5米……这些数字背后,是赵守峰把自己的训练心得编成口诀、把比武时的实战技巧拆成步骤、手把手教给队员的坚守。
在训练中,有的队员像赵守峰当年一样,累得把自救器和灭火器扔在地上,赵守峰把当年老队长教育自己的话用同样的语气教育新队员,让队员深深体会到“救援不是任务,而是生命托举的责任。”
“救援现场容不得半点侥幸。”赵守峰常说。在一次模拟矿井透水演练中,他带领队员反复推敲最佳救援路线,用秒表卡着时间优化每一个动作;在心肺复苏训练中,他总结出按压深度看指节、频率对准秒表的实用技巧,让队员在考核中全部达标。
从“娇惯新兵”到“救援尖兵”,赵守峰用“跟我上”的担当代替“给我上”的要求,用“传经验、教技巧”的耐心代替“讲大道理”的说教。正如他常说:“救援队伍的血脉传承不在口号里,而是在每一次同训同练的汗水里、每一次并肩冲锋的身影里。”如今,这支年轻的加强小队已成为救护大队的尖刀力量,而赵守峰的“传帮带”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公司救护队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被誉为和平时期最可爱的人。“选择了矿山救护这一行,就意味着要比平常人有更多的担当、付出更多的艰辛、担负更重的责任,尤其是当国家财产和职工群众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迎险而上。”赵守峰简洁有力的话语尽显他对矿山救护事业的崇高追求。